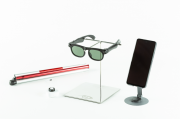原标题:隔代抚育的退场:现代夫妻关系下的育儿分工
在我国以家庭抚育为主流的早期育儿环境中,机构抚育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育儿模式首先通过育儿责任主体由内到外的延伸改变了男性在家庭内部的父职体验。笔者发现,在参与调查的13个家庭中,有12个家庭在将孩子送往日托中心前曾长期采用隔代抚育的照看方式,更有4个家庭在采用机构育儿的同时仍在接受祖辈在儿童抚育方面的日常帮助。隔代抚育是指家庭中祖辈成员参与照顾儿童的抚育方式,一般包括祖辈独立抚养或祖辈与父母共同抚养两种方式。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15]。

对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父母来说,面对日益高涨的育儿成本与生活压力以及精细化儿童抚育方式带来的育儿负担,通过求助老人来解决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从祖辈投入的育儿时间与精力来看,机构托育的引入大大减轻、转移了祖辈的育儿责任,隔代抚育正随着婴幼儿看护方式的社会化逐渐退场。而在祖辈退出抚养孩子的家庭工作之后,照顾子女的任务也落在年轻夫妻身上,围绕着抚育婴幼儿的家庭责任也开始在以现代夫妻关系为核心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并给男性带来了全新的父职实践。
1、从边缘到中心的父职体验
曾明(34岁,会计师)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孩子进入日托后自己育儿责任的变化。他的女儿萌萌在一岁六个月时进入贝儿日托中心,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已经退休的岳父岳母帮忙照顾。谈到“四大一小”育儿生活,曾明用“插不上手”来描述自己曾经的育儿体验。自己与妻子工作忙碌,岳父岳母几乎包揽了照顾孩子的所有重任,其中岳母主司孩子的吃饭、穿衣、午睡、日间玩耍、早教,岳父承担全家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开车带岳母和孩子外出遛弯、参加早教等其他任务。平日里夫妻俩下班后会陪孩子读绘本、玩游戏并陪伴女儿晚间入睡,却几乎没有单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谈到自己作为父亲所承担的育儿责任,曾明表示那时的自己只能被动地完成岳父岳母或妻子交代的任务,“女儿自出生起就被月嫂、岳母、岳父和妻子围绕,我却被排除在这个‘育儿战队’之外。想想自己为孩子所做的真的很少,也就换过几块尿不湿,收过她乱扔的乐高玩具,或者在下班路上买些她爱吃的水果”。这样的育儿安排一直持续到女儿一岁六个月,妻子89岁的奶奶因病卧床,需岳父岳母长期看护。为了解决家庭困境,妻子决定将萌萌送入离家不远的贝儿日托中心,曾明的育儿体验也就此改变。
“我很重要”是曾明描述自己现在家庭角色时一再强调的重点。“我确实很重要,因为我和妻子就像是完美契合的齿轮,需配合起来维持我们整个小家庭的运转。”离开了岳父岳母的帮助,曾明和妻子不仅要尽力维持此前的工作状态,还要接管照顾女儿生活起居、料理整个家庭生活的所有任务。这让曾明有了很多未曾经历过的育儿体验,他第一次独立给女儿洗澡,第一次了解女儿每日补充维生素D的用量,第一次给女儿网购了尿不湿。除此之外,他还在和女儿日益增进的父女互动中建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育儿职责。“女儿现在只要我哄睡,因为我会在给她讲完睡前故事后替她按摩一下头部、捏捏脚丫,常常是按着按着她就睡着了。其实我也教过我妻子该怎么做,但萌萌会说妈妈捏的不如爸爸捏的好。”曾明面带微笑地描述着属于自己和女儿的温馨时光。
从“插不上手”到“我很重要”,曾明的父职实践随着育儿方式的调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曾明来说,前期隔代育儿方式中祖辈的加入大大压缩了他参与育儿的空间,并形成了其被边缘化的父职体验。
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早期养育中,母亲和祖辈对婴幼儿日常照料的密集化与父亲照料的集体缺失共存,母亲与祖辈间的育儿协作使父亲们在较大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婴幼儿日常照料之外[16]。
这种边缘化的育儿体验不仅表现为育儿时间的不足,还包括育儿能力的低下。有学者认为,在不少采用隔代抚育方式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牺牲型父母角色”的过度角色化正成为窄化青年人生活能力、限制青年父母进入父母角色并承担起育儿责任的重要原因[17]。在祖辈的介入下,年轻父母需面对自身由孩子到父母的身份转化的困难,并极易陷入代际间的人际张力之中。这种集情感性与功利性于一体的联合过渡性抚幼模式正将年轻父亲推离育儿责任之外。
在此背景下,机构托育服务在缓解祖辈育儿压力的同时,也改变着由抚幼催生的扩大家庭结构。在机构的参与下,祖辈的退出为年轻父母让出了家庭内部的育儿空间,机构支持则进一步消减了年轻父母对祖辈的功能性依赖,提升了核心家庭的整体育儿能力。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人,他们有机会在独立育儿中学习照顾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技能。因此,对曾经被边缘化的父亲来说,祖辈的退场使他们有机会回到育儿工作的中心,并通过全新的育儿分工调整自己的父职实践。
2、现代夫妻关系下的育儿分工
自萌萌进入日托后,曾明用“配合战”来形容自己和妻子的全新育儿安排。在岳父岳母离京后的最初两周,夫妻二人需同时面对萌萌在日托中的不适应以及二人独立照顾孩子时的各种突发状况。在此期间,曾明也第一次意识到照顾萌萌需兼顾如此繁杂的琐事,并开始熟悉各项工作的操作手法与安排逻辑。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二人已逐步形成了根据彼此的工作时间、工作弹性、擅长的育儿内容来灵活调节各自育儿任务的家庭分工。
从育儿内容来看,萌萌的吃饭、穿衣、洗澡、家庭中的各项家务被列入需两人共同承担的一般育儿职责,教育、玩耍则根据夫妻二人的擅长项目各有分工。例如,曾明因有多年海外留学经历英文发音标准,故主要负责萌萌的英文启蒙,他会给萌萌读英文绘本或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与萌萌的英文对话。妻子有多年音乐学习经历,所以负责教女儿唱歌跳舞。而在笔者调查期间,适逢曾明的妻子刚刚通过在职研究生的答辩。曾明决定让妻子休一周的年假和朋友一起去普吉岛毕业旅行,其间由自己独自照顾萌萌。他坦言在过去的三年中,妻子辛苦孕育孩子、努力工作的同时还需继续求学,希望这个快乐的假期能让她放松一下,毕竟妻子的好心情才是他们小家庭奋斗的动力。
曾明与妻子“共同承担、各有所长”的育儿分工原则颠覆了我国传统家庭中育儿责任分配时的性别化逻辑。传统中国家庭在抚育儿童时虽采用的是双系抚育的方法,即为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对孩子全盘的生活教育,男女两性都应参与到抚育行动中,但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两性间的分工差异却并非来自男女两性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别,而是取决于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的分工体系。费孝通用“严父慈母”来概括这种抚育责任的划分[18],认为母亲应负担生理性抚育的责任,如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父亲则应担负起孩子社会性习惯养成的任务,像是道德教育、人格的培养等等。这种性别化的育儿分工方式在现代中国家庭中依然存在。
而受密集母职的影响,女性不仅从时间上对孩子紧密陪伴,还从职责上增加了母职的整体权重[19]。这也意味着从衣食住行到社会化教育,女性需负担的育儿责任已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父亲的责任则被进一步削弱,并开始形成引发社会诟病的“父职缺席”现象。
而无论是“严父慈母”还是“密集母职、父职缺席”,以上两种性别化的抚育分工方式都背离了我国现代家庭的发展趋势。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家庭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正朝向核心化、平等化以及感情中心化等现代家庭的模式发展[20]。在此前提下,现代夫妻关系也开始成为家庭内部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在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家庭关系中,平等型夫妻关系取代主从型夫妻关系,夫妻共同掌握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力,婚姻中的精神内容也越来越被重视[21]。因此,在试图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抚育责任分配逻辑时,平等化、合作式、情感性的夫妻关系开始成为育儿分工的全新方向。在此背景下,父职与母职的划分也将超越男女两性间的社会性别建构开始成为去性别化的亲职分工。在亲职责任中,父亲需与母亲共同承担家庭内外的育儿责任,并负担儿童成长各阶段的身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