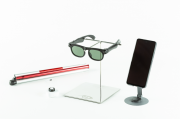原标题:非京籍娃娃:离京不得不做的选择 返乡又是学籍的漩涡
离京返乡一年后,刚上完初一的孙俊峰将被学校劝退,理由是他在寝室玩手机。孙俊峰曾在北京海淀区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因在京高考无望,于去年八月提前返乡就学。
这一结果出乎何冉的意料,印象里孙俊峰并非惹事之人,玩手机也不会严重到退学的地步,唯一能让她想到的只有“成绩”。
何冉是新公民计划流动儿童小升初团体追踪项目负责人,过去一年,她跟踪了孙俊峰在京所在班级小升初选择后的变化,25个返乡的孩子中,几乎均出现成绩下滑的现象。
不过,学业的变化只是冰山上可显见的一角,更多的隐忧还在冰山之下。对于大多数在京打工子弟家庭来说,在京升学没有出路,返乡则意味着变数。在适应和建立新的关系网络上,他们常常手足无措。
据新公民计划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2017年,在京小升初非京籍学生减少了23411人,占当年非京籍小学毕业生总数的45.5%。
何冉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会选择返乡就学,但她好奇他们会经历些什么?改变又会如何发生?

离京——不得不做的选择
六年级上学期,一直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孙俊峰得知自己要返乡就学,他问妈妈能否一起回去,母亲说:“回去的话,你爸要一个人挣钱养我们俩,而且你哥也还没结婚”,孙俊峰不作声了。他爸爸在麦当劳送外卖,每天晚上八九点出门,早上九十点到家,几乎全年无休。
孙俊峰自小生长在北京,一家三口在北五环的清河南镇租了1500元/月的单间,房间内只放了一个上下铺,上铺堆满杂物,1.2米宽的下铺是妈妈和孙俊峰晚上休息的地方,地上则铺满了行李,“感觉随时要跑路的节奏”,何冉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地坐,只能站着跟孙俊峰讲话。
样板学生的留守经历,图源:新公民计划
十四年来,除了极重要的事,孙俊峰鲜少回到家乡河南省驻马店。在孙俊峰的班里,近一半学生在北京生长,他们随着父母务工的脚步在北京市各区辗转,有的已四五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何冉从去年3月就选定了这所有700多人、九年制的打工子弟学校里一个即将毕业的六年级班级作为访谈、观察和记录的样本。
她统计了这个班同学毕业后的去向,43人里,只有18人留下,包括3名去河北上学、1名进了北京的公立校。剩下的25人皆返乡就读,其中超过一半都希望留在北京。他们的父母普遍从事着保洁、外卖、建筑工等工作,具有大学学历的只占极少数。
家长们很清楚,囿于政策,在京的打工子弟未来只有中职和高职两条路可走。家长担心,学校随时会像他们居住的群租房一样,面临拆迁的危险。除此之外,每学期涨五百、一年近万的学费对务工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
返乡虽可提前适应老家教学,为中高考做准备,但这个决定并不好做。
陈秋菊和丈夫来京十来年,在一所大学里承包报刊亭,孩子8岁前都由在河南老家的爷爷奶奶带着,成绩并不理想,来京后又在公办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之间辗转,成绩未有起色,陈秋菊对此颇有遗憾。但一起返乡的话,家里的生活来源会成问题,若铁了心让孩子独自返乡,则寄宿环境,学习节奏等能否适应?
为了减少这个顾虑,田苗的妈妈是少数几个下决心回乡陪读的家长之一,“我要把孩子带在身边,生了就要好好教”,她很早便打听着家乡学校使用的教材,让女儿闲暇时先熟悉一下。
这也是何冉要观察和记录的事情,她曾经为全国各地上百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接触了上万流动儿童,对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现状颇为清楚,但还没有对返乡的流动儿童的生活变化有过细致的研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结论,但没人知道这些变化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返乡孩子监护情况,图源:新公民计划
据何冉统计,返乡孩童的监护人中,有14个是祖辈照顾,父母双方或单方监护的共有5个,独自返乡生活的也占了5个。有一个需要亲戚轮流照顾,孩子父亲在老家有六个兄弟姐妹, 用孩子的话说,“周五放学这一天,我不知道站在校门口的是谁”。
返乡——学籍的漩涡
返乡之旅并不顺利,大部分学生第一步便卡在学籍上。
何冉曾记录,李依依的家人曾为她找到安徽当地升学率还不错的私立中学,依依的英语成绩优异,对于小升初面试英语口语测评颇有信心,但结果却落榜了。
依依家人找到学校老师请教后得知,其提供的学籍表没有学校盖章。“报名表上填的是北京XXW学校,学籍表上显示学籍在河南的JQ学校,名字也对不上,而且这两所学校都是民办学校,显得很不正规”。而其他从上海、江浙公办校转回来的孩子手续齐全,基本都录取了。
李依依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学生学籍被挂靠在河南当地一所民办校,这对当地学校来说或有经费补贴,但此举游走在法规之外,盖章留痕的事难度颇大。何冉认为学校只提供挂靠学籍的服务,至于转学籍和盖章的事学校基本不管。
学籍同样也让同样回安徽的田苗的妈妈吃尽苦头,田苗原可按老家划片进入镇上中学就读,但为了更好的教育,她妈妈托人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借用房东的房产证办齐了县城公立校入读手续。
不曾想,这所学校要求外地转学回来的学生必须出具“转学证明、学籍卡及当地教育局的盖章”。
田苗妈妈先后两次找了北京学校的校长,但被告知跨省转学通过网上就可操作,且学校开不了证明,但家乡的人告知,没有这些材料学校进不去,多方挣扎下,田苗妈妈还找过何冉,请教是否可以从网上下个公章下来,但被何冉拒绝。
无奈之下,田苗妈妈找到河南挂靠学籍的那所学校,但被学校老师告知,章在法人手里,可她找不到法人,他们开始拜托老家的人寻找河南教育体系里的“关系”,对方查了田苗的学籍后发现,田苗已于2017年7月毕业结业了,入学要直接上初二,这让田苗妈妈慌了神。
孙俊峰也卡在这上面,因为成绩不理想,他爸爸曾让孙俊峰留级一年,但他不知道无特殊原因政策不允许留级,也就没走申请。返乡时,孙俊峰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直接上初二,要么回原校找校长及当地教育局写证明盖章。但从上述情况看来,后者难度很大。
李依依和田苗兜兜转转,动用了不少关系,可算入了学,孙俊峰也进入河南泌阳县一所公立校,但学籍的事仍然悬而未决。
适应——互扇耳光变得顺理成章
进入家乡的学校对返乡的孩子来说才刚刚开始。
回到内蒙赤峰一所公立校的李忠进校第一天就被拦住,保安让他回去换身衣服,理由是他的牛仔裤破了几个洞,这身衣服是他特意为回乡备的。他的家境较好,常常一身运动名牌,家里找着关系让他进入该校火箭班。
那段时间,李忠比较封闭,不想与别人交流,“他们就觉得我在装高冷,靠关系进入火箭班”,对方爆了粗口,两人打了一架。孙俊峰也会遇到“北京来的了不起呀”的挑衅,但他并不认为同学心怀恶意,这与他见到同学乱扔垃圾、频爆粗口时觉得不适应一样。孙俊峰性格内向,他所在的学校有一千多人,班级人数60余人,但到现在,他也未与班内大部分女生说过话。
何冉说,北京的生活多少都会给流动儿童留下印记,网购经历、行为举止以及着装常跟家乡的学生形成差异,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会因此而难觅到好友。
孙俊峰知道家人送他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他努力过,“是真学不懂,没有人告诉我方法、要怎么样学,也跟不上”,前两次月考中,孙俊峰除了英语及格,其他全部挂了“红灯”,
有一次,何冉去学校找孙俊峰,被数学老师当作他有“亲戚关系的姐姐”,在教室门口,何冉被训了一顿,“你们这些家长是怎么当的,就把这个孩子扔家里头,什么也不管,学习这么差,作业也不做,把我们班上的分都拉低了,我都不知道找谁,为什么把他送回来?”
何冉回:因为在北京没办法考学,没有学籍。
数学老师说,“那不重要,只要成绩好,初三也可以回来考。你现在把他送回来,丢在家里,你觉得能考高中吗?”
事实上,每周末孙俊峰的妈妈都会打电话给他,还曾想着为孙俊峰报辅导班,但从家里到县城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学校周末又不提供住宿。
在没有各方的支持下,孙俊峰的成绩下降几乎成了必然,而在北京常考第一的苗苗回了安徽老家的一所私立学校后也被浇了一盆冷水。第一次月考,因为六年级的教材两地并不一样,她的数学只考了66分。
据项目组对比返乡和留京两组同学的课业后情况,返乡组比留京组平均每天要多出4节课,写作业时长多出2个小时左右,老师要明显严厉的多。
在中国的很多县域,应试仍然是学校的主流,升学率常常成为硬指标,老师的绩效与学生成绩有直接关系,因此催逼出的题海战术、惩罚性措施花样百出。
苗苗的英语老师会抽查单词,不会写的会要求同桌扇耳光,响声太小的话老师就要亲自动手,刚开始,苗苗觉得这让人很难堪,但规训久了,看到最好的学生也被打,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而因为成绩不好、作业没完成而“挨板子”的事情在返乡的学生中不在少数。
这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近乎放养的状态有所区别,留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初一的宁宁说,老师看起来很忙很累,不太重视学生,“上一会儿课会让我们自习”。宁宁的成绩很糟糕,他说爸爸“不指望我考大学,让我留京考个高职”。
何冉说,这与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缺乏支持动力有关,“北京公立校生均经费数万,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费用则大部分来自市场”,学生每年数千的学费对解决师资提升、学校建设等各方面问题是杯水车薪。待遇一低,好老师留不住,只拥有中专大专学历、跨学科、跨学年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学校更多地在履行托管、看护的职能”。
以学业为重的家长们明显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感到不满,但何冉也强调,从课程丰富性上来说,由于社会组织的补充,一些素质类课程也会进到打工子弟学校里,相比老家纯应试的学校来说,“素质教育的底子还是有的”。
在新公民计划组织的返乡儿童暑期活动中,十几个返乡学生在分享理想中的老师时,大都希望能有个严师,能镇得住学生,鲜少涉及老师的业务能力层面。
逃离——习惯同伴失去和不习惯的亲情
刚返乡时,孙俊峰的周末是在哥哥单位提供的一间休息室里度过的,他说哥哥指导过他学习,自己不会的时候,哥哥还老对他动手,常常念叨学习的事情让孙俊峰感到厌烦,但不久哥哥因工作被调到市里,孙俊峰要独自返家,这对从未在老家生活过的他是不小的考验。
第一次从县里坐大巴回家时,孙俊峰不小心过了站,哥哥开了五个小时的车才在深夜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子里找到了他。
孙俊峰的家是个二层小楼,他父亲觉得,孙俊峰长这么大,生活应该能自理,但事实并非如此。何冉到他家时,天气还有点冷,她发现孙俊峰的床没有褥子,他也不会做饭,饮食上毫无规律,饿的时候到镇上的超市买点零食和速冻水饺,小卖部的收银员是他亲戚,他叫不出名字,每次只是微笑、点头、付账。
孙俊峰的周末宅在家里,就像在北京的家里一样,活动的范围只在周围数公里之内,与邻居鲜少走动,像是生活在一片孤岛。孙俊峰手机不离身,游戏玩的腻烦时也会有孤独感涌上来,可他仍不主动与北京的朋友联系,何冉注意到,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一个留在北京的学生曾向她抱怨返乡的几个朋友明明显示qq上线了,动态上还有游戏截图,可就是不回他的信息,所以他也不想联系了。
何冉曾问过孙俊峰,他的回答是没时间看手机,可何冉的信息他回的却很及时。她也注意到,有四五个返乡后的学生悄然退出qq群。何冉看过关于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同伴关系”上的相关研究,返乡孩子的“同伴疏远”得分显著高于留守的农民工子女。
何冉向芥末堆回忆起去年四月份,她提前进校观察那些即将返乡的孩子们的情绪,但发现并没有太大波澜。她推测,长期流动、频繁更换居所和学校的孩子,可能已经“习惯随时会失去同伴”的状态。
但离乡十几年,想让疏远的亲情迅速着补回来可不容易。晴朗返乡时,暂住在大姨家,七十多岁的爷爷从乡下骑了三小时的三轮车来看她,想挨得离孙女近点,但晴朗侧瞄着爷爷,往沙发外挪了挪,接着拿着手机跑了出去,在一旁观察的何冉起初觉得很气愤,认为晴朗不尊重人,但晴朗说,她没和爷爷生活过,感觉很怕他,而另一位小伙伴则觉得,照顾自己的祖辈有重男轻女的情况,觉得“除有必要,其他时刻都不想和他们交流”。
抗拒和逃离,似乎是他们面对新环境时常会做出的应激反应,而更多时候是无所适从。
一位返乡的孩子因为周一晚自习从老家出发来不及,要在外公的兄弟处住一宿,何冉观察到,孩子在客厅里,很不自然,“如坐针毡,比我还拘谨”,亲戚常买些零食放进孩子的书包里,但家里的小孩会去扒拉他的书包,从中拿走东西,但他不会去制止,理由是:我住在别人家,他拿点东西难道不应该吗?
不断受锤的牛:“如果没有办法,那就这样吧”
“返乡孩子经常会把自己从社会关系中拎出来,与身边环境做区分,缺乏在新环境里去应付或建构新的社会网络的能力”,何冉说,父母也很少或没有能力教他们应对这些状况。但孩子们寻求帮助的渠道,往往不是家长和老师,而是手机。就像一位返乡陪读、缺少朋友的母亲一样,微信的朋友圈里情感类的文章陡然增多。何冉曾让孙俊峰在手机和父母的重要度上做出排序,孙俊峰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相比之下,具有留守经历的孩子对返乡的接受度看起来更高,更愿意和隔代相处,何冉接触的学生中,有表示老家更方便的,还能顺便帮忙照顾年长的祖辈,也有的说返乡后“被父母紧逼学习的压力小了”,当然也有吐槽“在北京卖菜的父母每天早起,自己周六日在家不能打扰他们休息、找不到人说话”的那种孤独,在他们眼里,返乡和爷爷奶奶待着似乎更舒服。
何冉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从小在北京长大并返乡的孩子,平均每周和父母通话或视频次数及时长均远超有过留守经历,小学后才被接到北京并再次返乡的孩子。而大部分返乡的孩童中在一年之后,都更愿意返回北京就读,当然,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而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曾经有过流动儿童经历、在京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长时间与父母的分离,返乡后的无所适从,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其恶果渐渐在孩子身上显现,颓废感是何冉从这些孩子身上常看到的,他们好像接受了加诸己身的各种不如意,“如果没有办法,那就这样吧”,就像不断受锤的牛一样。
铭泰新学期也要返乡了,此前为了照顾弟弟,她在北京继续念了初一,为了能跟上家乡的教学进度,家人让她留级一年,下学期回到四川南充跟舅妈住一起,在大街上,芥末堆问她对北京生活的印象,她回了一句,大意是北京的一切都跟梦/玻璃一样,消逝、易碎。铭泰几乎参加了所有在京的返乡学生暑期活动,仿佛要抓住最后的记忆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