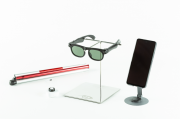原标题:对于“教育学理论”,信息技术改变了什么?
所谓“改变”,在这里,意味着一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有了信息技术和没有信息技术,教育学理论,有何不同?这种“不同”是只有信息技术才会带来的“不同”。
与其他学科理论形式一样,信息技术带给教育学理论的改变,通常表现在成果的“存在方式”“表述方式”和“传播方式”上。

第一,形成了多元化的存在方式。当前的“学术论文”,至少有四种存在方式:“第一是纸媒体存在(通过学术期刊);第二是互联网存在(通过博客、微博等);第三是数据库存在(通过中国知网等);第四是公众号存在。”(赵勇,2017)除了“纸媒体”之外,其他三种存在方式,都是信息技术带来的。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已然成为当下学术文章的“新宠”。能否,以及通过何种公众号来推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章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这方面,教育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已经基本上做到了“同步跟进”“同时并举”。例如,《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教育类学术期刊,大都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把每一期发表在纸媒体上的重要论文也即时推送。
第二,形成了多维化的表述方式。传统学术论文的观点和见解,是以相对艰涩或枯燥的专业术语、统计数据、图表公式和玄奥莫测的考据、引证等方式表述的,它们主要由文字构成,是一种文字化的“单维结构”。但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存在方式之中,增添了“图片”“视频”“音频”,文章变成了一种“多维结构”,融语义、听觉、视觉和行为于一体,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媒介的延伸”,即从“文字媒介”到“视频媒介、图像媒介”的延伸,也是“思想传递的延伸”,即从“文字传递的思想”到“视频图像传递的思想”的延伸。表述方式的“多维”,不全是文本形式的多维,也不只是符号结构的多维,视频与图像符号同样成为理论文本符号结构中的主体,更内含着“表述逻辑”的多维,体现了“文字逻辑”与“视频逻辑”“图像逻辑”的交织(李政涛,2017)。在此过程中,一种新的学术文体已经呼之欲出,这是信息技术催生的多维表述方式和表述逻辑共同编织而成的新文体。
第三,形成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相对于“知网”等数据库,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产生,首先恢复或赋予了理论知识的阅读本性或传播本性。“知网”主要供人查阅,“微信”更多是供人阅读和传播推广的。其次,它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例如,“微博”已成为信息传播中“对媒体软环境有着颠覆性影响”的新平台,在学术期刊的编读互动及读者参与和分享方面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博客媒介也从网络扩展到手机、印刷、出版、广播、电视等各个媒介渠道,催生了“期刊微博”的运营方式。又如,同样作为学术信息传播的新平台,手机报或网络电子版等,凭借其丰富且新颖的传播策略,让“小众学术”走进“大众视野”(夏登武,2016)。第三,它拓展了学术期刊的新闻报道功能。信息技术时代的科学研究,在保留学术底色的同时,新闻性的一面也愈加凸显。《Science》杂志与美国专事报道科技新闻的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美国科学促进会下属的EurekAlert 网站向全世界的记者发布论文成果。2006年,《Science》刊登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尤海鲁关于鸟类化石研究的论文,并将这一重大科学发现撰写成为新闻发布,很快被全世界的大众媒介转播,使得该科学家和杂志的名字伴随科研成果一同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高健,陈新石,游苏宁,2008)。2007年,中国科协率先在国内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为科研学术成果的新闻传播架起了第一座桥梁。科研成果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有利于扩大科研成果、作者乃至期刊影响力。有研究显示,进行过新闻报道的文章的网站点击率与下载量明显高于未进行过新闻报道的文章,如经《纽约时报》报道的论文,一年内的被引用率增加了72.8%(吴淑金,2012)。最后,它造就的新的传播模式,除了强调快速、便捷的新闻性之外,参与化、互动化的特性越发凸显,“造成了文化传播从传统媒体时代的‘我写(说)你看(听)却无言’的单向专断模式,向当下‘我写(说)你看(听)大家传’的多向互动模式的嬗变”(魏建亮,2014)。
如上对于信息技术带来的理论研究改变的分析,主要是在媒介或工具的意义上展开的,尤其是媒介的改变,为教育学理论带来新的阅读媒介、写作媒介、交流和传播媒介。这些媒介本质上被视为“工具”,例如,成为“学术期刊可视化”的工具(张新玲,2017)。
在我们看来,这些改变还只是浅层或表层意义上的改变。已有的相关调查与研究,总体上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以对“学术微信公众号”发展状态的研究为例,相关研究的目的与主题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平台之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刘婧,魏建香,2015)、“策略”(冀芳,张夏恒,2016)、“效果”(张小强,吉媛,游滨,2018)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于学术发展的“质量”(李宇佳,2017)等展开的。
在教育学界,相关的研究为数不多,且主要限定于“信息技术与教育研究”的层面。有的是以“教育类CSSCI学术期刊”为例进行传播效果分析,指出“学术期刊微信平台高质量原创比率较低、周期内发文数量与传播效果不呈线性关系、微信平台对于推送传统编辑形式学术论文传播效果甚微”等存在问题,提出“丰富编辑形式,增强与受众互动,注重数据分析,拓展推广渠道”等运营对策(赵文青,宗明刚,张向凤,2016);有的把信息技术作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条路径,探讨信息技术背景下的“科学计量方法与技术”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应用”(蔡建东,汪基德,马婧,2013)等。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和落脚点,或是“信息技术本身”,或是“信息技术工具的运用及其结果”,基本上没有进入“教育学理论”领域,更没有从“理论生产”的角度,探究信息技术与理论发展的关系。曾经有人从传播的角度阐发了微信公众号的学术价值:“虽然它们推送的是纸媒上发表过的文章,但这些文章经过微信公众号的编辑制作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叫做学术话语的再传播,也可以叫做学术话语的再生产。”(赵勇,2017)这里指明了传播方式的变化,推动了理论话语的再生产,但仅限于此,并未进一步触及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带给教育学理论的是“深层”或“深度”改变,表现在“价值尺度”“理论边界”“生产机制”“理论主体”等四个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带来了新的“价值尺度”。
麦克卢汉曾指出,新媒介的出现,势必会引起社会生活、权力结构、媒介生态的变化,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价值尺度,催生思想重构,进一步改变话语结构的走向(麦克卢汉,2000,第33-50页)。
对于理论生产而言,新的价值尺度意味着新的评价标准或评价尺度。一旦信息技术时代教育学理论的存在方式、表述方式和传播方式等发生改变,会倒逼学术评价发生变化,向多元、多维和多样化发展。例如,“微信网络平台”上的学术评价,“更多的是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随感而发,或是基于微观察、亲身体验的个体评价,甚至是对欣赏对象的观点转述,其往往以随笔甚至是碎片式、跳跃式的形式写就。因此,微信网络平台上的学术评价在内容、范围、形式等方面都显得更加丰富”(路学军,2017)。不仅如此,这种由微信平台引发的学术评价形式与内容的日益丰富,将导致学术评价体系的逐步更新。
首先,是评价对象,即“评什么”的改变。比如,在“学术成果”的认定上,由原来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才被认可,扩展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重要报纸发表的理论性文章,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承认为“学术成果”,随后,在新媒体浪潮的推动下,一个新的变化趋势正在生成:不是只有发表在纸质媒体的理论成果才被评价体系接纳,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的原创性学术论文,也将有资格纳入“学术成果”,成为被评价的对象。
其次,是评价主体,即“谁来评”的改变。原先的评价主体主要是“同行”“专家”“专业领导”等,均属于“象牙塔”的顶尖人士。而学术成果一旦进入微信公众号,在阅读者和评价者数量大增的同时,也改变了评价主体的结构。更多不同职业、阶层的人在阅读、理解和认同的过程中,也在不知不觉间拓展了评价主体的结构,它带来了一个不再自诩“学术小众”“曲高和寡”而是比拼“阅读量”“粉丝数”和“传播面”的学术评价新时代。
再次,是评价标准,即“什么是好的学术成果”的改变。由于视频符号、图像符号的广泛运用,那种纯文字的单维表达,将让位于多维表达或复调表达的理论成果(李政涛,2013)。善于运用视频和图像来阐述观点、分析问题,也将成为“好论文”的新标杆。
第二,信息技术拓展了原有的 “理论边界”。
这一“理论边界”包括知识边界、问题边界、概念边界、方法边界等。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强势渗透,不仅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知识的内涵与形态”,也会让我们重新提出并思考在信息技术时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势必会有各种答案,但至少对“知识的信息技术内涵”“信息技术型的知识”等与知识和技术有关问题的探究与回应,将作为信息技术时代新的知识论基础,为当代教育学理论重新奠基,促使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等共同反思自身的知识型态与内蕴的自我更新,推动理论知识再生产。
知识边界的拓展,会引发教育学理论的问题边界与概念边界的拓展,至少与信息技术有关的问题或概念将纳入原有的问题域。在当代,一个对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问题或概念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甚至全然排斥的理论体系,注定会在“自娱自乐”中走向“自我封闭”“自我隔离”乃至“自我消亡”。问题边界与概念边界的拓展有两种情形:一是增加新问题和新概念,例如“人工智能”“指数思维”(祝智庭,贺斌,2012;祝智庭,2016);二是对老问题、老概念提出新思考,赋予新内涵。例如,“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触发了人们对“什么是‘人’”“什么是‘教育’”等“嚼不烂”的老问题的再追问和再回答。同理,若把“教师专业发展”置于“人工智能”的背景下重新加以探究,新理论的产生将会“水到渠成”。学校道德教育的思维方式也会因大数据的加入而发生从片面到全面、从整齐划一到尊重个性、从片断化到连续化、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四维变革(张姜坤,王夫艳,2018)。
信息技术带来的“方法边界”的拓展,同样显而易见。借助微信网络平台的推波助澜,视频、图像等资料的规模化、持续化应用,导致视频、图像分析方法的日渐流行,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学研究容易陷入的思辨/实证的二元对立,而且也丰富拓展了对“教育实证研究”内涵及类型的理解(袁振国,2017)。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正在改变原有的“研究范式”,在经验科学、理论科学与计算科学之外,产生了第四种研究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它并不事先假定具有因果关系的模型,转而直接面向数据本身寻求知识的发现(陈明选,俞文韬,2016)。
如上理论边界的拓展,必将导致原有的教育学理论框架、理论体系的拓展与更新,迎来教育学新的理论格局。
第三,信息技术生成了新的理论生产机制。
这一机制包括纵向机制与横向机制两个方面。
一是纵向机制,即过程机制。以往有关信息技术之于“教育研究”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的“结果”。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理论研究的生产机制,尤其是深入到理论生产的“过程”之中,变成当代教育学理论生产的过程机制的一部分。以博士论文的撰写为例,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存在方式、表述方式和传播方式,已渗入从主题确定、资料搜集、文献综述、方法选择到论文撰写,再到论文评审、答辩,以及出版发表的全过程之中。不仅是博士论文,当今学者的任何学术著述,要离开信息技术提供的新媒体、新平台,都是难以想象的。在相当程度上,信息技术在深入到教育学理论生产的“骨髓”与“毛细血管”的同时,也再造了新的理论“骨髓”,创造了新的理论“毛细血管”。
二是横向机制。除了评价机制之外,还包括理论生产者之间的交往机制与合作机制。信息技术改变了学术圈的相互联结、信息共享、科研合作方式,构筑了新型的理论共同体或学术新社区。这些针对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学术社交媒体,国外如ResearchGate、Academia.edu、Mendeley等,国内典型如“微信学术社区”。它们的创建大都是以“学术组织”为载体,如“中青年教育理论分会微信群”“教育基本理论微信群”“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群”;或是以“学术会议”为契机,如“2019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年会交流群”“中国德育论坛”“徐州教育哲学论坛”等。还有的以“学派”“信念”“主题”等来命名,如致力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研究的微信群“以身立学汇”,旨在推动古典教育复兴的“古典教育研究群”等。此外,还有以“年龄”“身份”等为标志的微信学术社区,如“60后大学教育学人”“教育领域长江学者”微信群等。
这些内含了平等参与、多样化表述理念的“微信社区”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交往圈的角色、观念、规则,扩展了学术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网络成员类型的多样化水平,使得科研人员的交往网络更容易突破原有学术圈的限制,扩展至政府、企业等部门,以及拓展到别的学科,在带来更加多样化的学术信息和理论资源的同时,也促进了跨领域跨学科的对话交流,拓展了理论影响力的边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即时性和交互性,“一旦产生碰撞,形成热度,就很容易导致观点交锋,这是微信群有别于其他媒介的重要特质。如果能够有效地把握住微信群中话题互动所产生的学术探索机会,通过即时的理性辩论,就有助于深化学术问题,探寻学术真相”(路学军,2017)。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使用这些具有专业性、学术性的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的论文产出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朱依娜,2017)。
第四,信息技术改变了理论主体的生存方式。
没有什么比“人的改变”更能说明信息技术带来的“深刻变化”了。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上,信息技术带给教育最大的变化,不是教学工具、技术、策略与方法的变化,而是人的变化,比如,催生了“图像人”,这是信息技术带给教育的最大挑战(李政涛,2004)。同样,信息技术对于教育学理论生产最大的影响和改变,也是对“理论人”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对于他们而言,在信息技术时代做教育学的学问,不仅需要新技术、新方法,更需要新素养和新能力。所谓“媒介素养”,不只是教育学理论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也是理论研究者自身素养与能力的一部分。今日,尤其是未来的教育学人,善于运用多元化的学术平台,多维的表述方式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将成为他们的一种“理论新基本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其学术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发生在理论人身上的变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学术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改变,成为信息技术时代孕育出来的新型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前述博士论文的“生产过程”即可看出,当今教育学理论人的生活方式深深浸染了信息技术的气息,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如果要研究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内涵、标准和定义都将因为增添了“信息技术”的意蕴,而与以往有很大差异。
价值尺度、理论边界、生产机制以及理论人生存方式等的改变,汇聚起来,将会触发“教育学教育”体系的整体改变,从教育目标、知识形态、课程体系到教学方式等,都将打上“信息技术”的鲜明烙印。
由此生成的重大问题是:在信息技术时代,“教育学理论”如何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