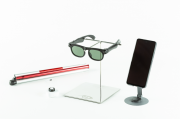原标题:内地高才 “自降身价”卷去香港
电影《甜蜜蜜》里,因为改革开放,大量内地年轻人涌进香港讨生活,底层出身的马小军语言磕绊,文化不通,但相信只要有手有脚,就不会饿死。

(图/《甜蜜蜜》)
近三十年后,面临本土人才的流失,香港继续揽才。又一批内地“打工人”通过高才、优才、专才等人才计划加入这座城市,带来新的融合与碰撞。
他们渴望摆脱既有的困顿,又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有人背上“工贼”的指责,有人依然在内地交着社保。“卷”的背后是不安,能在香港博取到什么,更多“高才”仍在观望。
内地精英,香港揾工
曾经,“香港梦”的注脚是,只要有手有脚,就不会饿死。但现在,对拥有骄人学历和职业背景的内地高才来说,揾工(粤语中找工作的意思)香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去香港工作前,广州人菲菲突击报班,学了两个月粤语。从小接触的都是普通话教育,后来又去英国读了本科、硕士,她不会说粤语。对于只有一江之隔的香港,她也感到陌生,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环境,都停留在加班到深夜、周末只有单休的TVB职场剧情节。
她申请上了香港高才通人才计划,在港工作7年就可以获得永居。对于28岁的菲菲来说,得到香港身份,意味能享受到教育、税务、医疗等一系列优势,170多个国家免签的通行自由,“人生总是选择越多越好”。
菲菲在Jobsdb、Glassdoor上投了100多份简历,只接到不超过10家公司的面试邀请。一路过关斩将,从HR、manager到大老板,至少三轮面试,有的环节还需要做汇报和介绍产品。“他们看重的其实还是学历、专业和留学背景,普通话也不是减分项。”在生物医疗行业,因为菲菲有从做research到市场的经验,最后找到了一家生物医疗外企的销售职位。

香港街道。(图/pexels)
在北京工作快十年的张晨,拖着两个箱子来到香港,花两天时间找房,一周内收拾好屋子,就入职打工了。张晨在大厂、广告公司都待过,2024年年初,她集中投递四十多家岗位后找到了工作。因为确实不了解香港的市场,也没有非常拿得出手的“global”的经验,没有优势申请“全球或者大中华区的业务”,她会去搜索mainland关键词,专门找针对内地业务的字眼。
其实,从北京离职后,她还去悉尼和大理度假,“gap”了近一年,发现“原来在北京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个世界很窄的一面”。她曾有有想移民的打算,但如果在澳洲工作,无论是文化还是身份上,都会有一些困难。更何况,她不愿意放弃过往的经历去做蓝领。那时,香港高才的申请已经通过,从职业发展的角度,香港就成了那个托底的选择。
香港正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从2019年起,香港人口连续3年下跌,本地居民净移出已经达到18.5万。另据香港总商会在2023年4月的问卷调查显示,74%受访企业反映人才短缺,当中逾八成表示情况已持续一年以上。
流失的劳动人口中一半为中高端人才,这也是香港这几年拼命揽才的原因之一。2022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计划”),这是目前获取香港身份最快的方式之一,一般4-8周就能获批,且获批率极高。类似的还有优才计划、专才计划,都会对申请人的学历、语言能力、职业技能、家庭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
高才的申请以高学历及高薪酬为主,要么全年收入达港币250万元,要么获得全球百强大学的学士学位,国内的高校目前已从9所放宽到了13所。截至今年5月底,港府已收到近8.5万份高才申请,获批数超过6.8万份。获批者中近九成都来自内地。

(图/pexels)
中年失业的第五个月,李雅芳看到复旦校友群里关于高才的讨论,决定申请高才,多一个出路。失业这几个月,超过35岁的她已被互联网大厂抛弃,中小企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申请香港高才对于她来说,和学英语以及做其他准备一样,不过是想让手上多一张牌。
申请流程非常简洁,在提交了学历、身份证明,并上传最近两份互联网公司的离职证明,近三年纳税证明后,李雅芳很快获批。但她并没有真正开始在香港求职,一方面孩子已经在北京上幼儿园,另一方面香港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松弛”的地方。那里空间狭窄、全球人才高度竞争、成本高企,10年前她第一次去的时候,在酒店门口问门童附近有没有星巴克,被高傲回复:I don't speak Chinese。拖家带口从北漂转为港漂,也是艰难的决定。
李雅芳的不少同学都获批了香港高才,但真正过去求职的很少。至于下一步该怎么续签,大家的态度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她也在关注去香港求职的朋友的动向。有位内地名校、海归背景和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朋友经历数次考试、面试后,依然在等offer。非金融、IT背景的她更没有信心去香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
这也是现实的另一面。香港的金融和外贸发达,但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白领工作岗位并不多元。“金融、计算机、律师、医生那些才能有钱赚。”一家香港公关公司工作的HR告诉每日人物,他们招聘公关助理,应届生的薪资是港币1万3,有三五年工作经验的是2万港币。“在香港,餐馆洗碗工一个月都一万五,厉害的护士一个月10万。”
社交媒体上,有人抱怨,近期投了93份VC(风险投资)还没有回应,“去年投还能接到3到5个面试邀请”。评论区,有人说投了200份简历,连优衣库、MUJI的销售助理、马会的养马师都投了,面试了六七个,终于有offer了。

(图/pexels)
准入门槛较低的保险业,成为很多高才的选择。三十多岁的吴达,曾经在头部投行和大厂投资部工作。身边人得知他要去香港卖保险时,都说他疯了。他经历过互联网大厂的清洗,一直记得,隔壁园区在一夜之间从人声鼎沸变成了“鬼城”。紧接着,他又见证了金融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保险是香港金融业里唯一逆势增长的。”他将保险视为顺势而为的选择。
吴达的主要客户在北京,因此他依然住在北京,需要签单时才去香港。乘坐晚上八点从北京西站发车的G79次列车,第二天早上就可以从香港西九龙站走出来。
还有很多高才计划的申请者,出于各种原因,过着往返不同城市的双城生活。
26岁的Michael,2020年从985高校理工专业毕业后,拿到了一份年薪20万的大厂offer。工作2个月,他就因为无法忍受所在部门加班、内卷、勾心斗角的氛围,选择离职。后来,他转战商学院,做起了大客户销售。2022年12月底,高才计划推出时,他本来已经打算回北方老家。高才通获批后,他加入了一个“都是一群能量很高的人”的保险团队。
考虑到香港租房成本太高,Michael选择住在深圳。每逢周一开例会的日子,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穿着长袖、长裤,套上西装外套,出现在香港海港城。
菲菲住在深圳,是因为她养了两只猫。香港的宠物防疫政策严格,内地宠物至少需要隔离120天才能入境。十点上班,菲菲每天八点半在福田口岸过关,她特意把斜肩包换成了双肩包,这样装上电脑和水,可以更加省力。她还特意带了一个零钱包,里面必备500港币现金,因为在香港打车现金支付还是主流。
没人想当“工贼”
优才、高才去香港工作,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的说法是——那些便宜又听话的内地“工贼”,将不好的工作风气带入了香港职场。在媒体报道中,有香港HR吐槽道:(他们)是不是有问题,是家庭不幸福、能力有问题、精神有问题还是诚信有问题,为什么不把自己当人看?
几位高才都不喜欢“工贼”这个标签。没有人喜欢卷,甚至申请“高才”,就是为了逃离“卷”的环境,寻求通往更广阔的天地的跳板。
进入新的环境,每个人都从习惯性的紧绷和察言观色,逐渐放松下来。

(图/pexels)
一个周一的早晨,菲菲因为手机出了故障,赶不上公司十点的会议,只能先线上参与,开完会她表示会抓紧赶到公司。还是老板主动提出,外面还在下雨,既然已经开了会,中午也准时到了,上午就不用算请假了。还有一次,需要九点就去公司,老板考虑到她的通勤,特意询问那个时间是否合适。
这些变化冲击着菲菲的“班味儿”。菲菲在深圳做过2年基因研发,又去广州做了近1年的市场和产品,曾饱受加班文化的困扰。
她一直记得,有次开车回家过周末,她一边握住方向盘,一边参加视频会议。刚刚生完孩子的领导,在给大家安排工作。她气愤又无奈:“领导不那样,会担心自己被炒。所有人都在被折磨,这种感觉让我很难受。”
来香港公司做销售,菲菲主要面向的是大学实验室、政府和私企。刚开始,她不熟悉业务,也搞不清楚供应链,“各方面都有点迷糊,经常找错人”。作为当时部门唯一的内地人,都是同事们告诉她具体流程应该怎么走。销售有业务要求,但公司并没有给很大的压力,“因为我的稳定也是老板的考核指标,大家会有一种一起成长的心态”。
香港的职场讲究专业和效率,工作忙碌,但非常注重员工权益的保护。香港政府设立了一个“在香港就业”的官方网站,除了细致展示求职资讯外,还涵盖有劳工法例、雇员保障、职业安全等信息。
女性友好是吸引菲菲的另一大因素。以前作为销售,难免参加一些应酬,在由男性主导的场合中,曾有代理商跟她说:“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可以过来坐到医生的大腿上。”香港公司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和客户之间也都是公事公办,“私人的酒桌,以及附带的职场性骚扰终于不再有了”。

(图/pexels)
吴达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一直紧跟行业风口,也亲历了从拥有一切到回到原点的过程。互联网大厂疯狂裁员,吴达带的团队,被HR“摁着”,“把大家都给裁掉”。紧接着,金融行业也开始裁员和降薪。到现在,他每次在国贸和投行的朋友们吃饭,都觉得极其低气压,“我跟他们开玩笑,吃一顿饭回来要三个小时自我疗伤,太丧了”。
对比之下,在香港的生活状态能让他暂时逃离焦虑。在北京,吴达一家周末十点出发去香山,可能十一点半还在山底下找停车位。而香港面积的四分之三都是郊野公园,如果住在中环附近,很快就能从码头乘船到离岛上去爬山。
有人在享受香港职场氛围的同时,被香港HR吐槽的“卷”也确实存在。
高才申请属于宽进严出,后续能否续签,甚至熬够7年获得永居,关键还是要看申请人能否在港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有没有纳税。一些高才、优才为了续签,要么挂靠中介,要么给自己买保险获得提成。但这些方式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合格。更严重的,还可能被驱逐。
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和续签机会,一些高才、优才主动“自降身价”。
在香港某传媒公司做运营的木子确实发现,他们收到一些来自内地的简历,主动标明了“24小时on call(随叫随到)”。她的老板会专门请一些内地人来做兼职,前段时间,公司刚刚招进来一名优才,还在试用期,一天20块一个小时,这已经低于本地人的薪资,但那名优才却很开心。
Doris在一家中港两地招聘公司做了20多年人力,因此比较清楚香港劳动力市场,以及雇主的想法。她说,少部分公司才会招很“卷”的人,毕竟,“只有医护,警察之类才会24小时on call,普通文职工作,或者劳务都不需要。”

香港步行街。(图/pexels)
他们公司招聘的高才优才,也是以保险,家办(家族办公室,金融投资领域),医疗行业最多。如Doris所说,雇主们也想发展内地市场,大家对于内地才人的需求,最看重的还是经验、态度,以及稳定性。
为了获得工作入场券,很多人选择去做保险经纪。
入职最开始的两个月,Michael每天都举着牌子,在室外站四五个小时,向路人推销保险产品。这就是行话里的cold call(上门推销)。初入职的员工都要放下架子,“克服很大的心理难关”。一个大雨天,第一位客户找上门来,他们从下午4点聊到了晚上9点,Michael成功签下第一单,分到了十几万提成。
行业里不乏年薪百万的故事,Michael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7年后拿到永居,10年内要在香港买房。
留下的、离开的
做一场“香港梦”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并不低。乘着政策之风,即便拿到通行证,站在去往新生活的路口,很多人依然对前方的道路感到茫然。
很多赴港人才,看重港籍生的升学优势,是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来。他们舍弃了原先体面稳定的生活,需要重新寻找工作,支付高昂的生活费与房租。一个小两居,一个月至少也要2-5万港币,再综合各种教育成本,一年可能需要50万打底。
不只是花钱那么简单,很多去香港的陪读妈妈被逼成了“教育专家”。42岁的小娟,为了给上初中的孩子选择学校,忙碌两个月,最终以“插班”失败告终。她的目标是让孩子进入排名靠前的band 1学校,香港有官立学校、津贴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家长要分门别类地准备申请材料、参加面试,孩子也参加了十几场考试。
这个过程中,小娟深刻体会到香港本地精英对教育的投入,与内地中产相比不遑多让。“不卷学区房,但更考验孩子的学习能力、家长的择校规划能力还有跑腿送简历的体力。”灰心之下,他们只能在暑假后再重新申请学校。
除了教育上的竞争,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香港本地人也感受到房租涨价、薪资下降的压力。

(图/pexels)
木子是香港本地人,她的家人排队20多年,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月租大概5000港币,这已经属于福利房的最低价格了。还在读硕士期间,她就开始做各种兼职挣钱,“香港文化就是大学自己工作赚学费,爸妈一般不管你,工作后还要给家用”。
去年她毕业后,发现香港的工作环境也不如以前了,工资更低了。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找一份普通工作,薪资已经从原来的1万5港币,降到了现在的1万2左右,这个月薪,以前在香港几乎不会有人做,“因为是最基本的生活成本”。
以前的港片里,充满草根逆袭的神话,“但事实上,很多人就算奋斗10辈子,也住不到太平山上”。
而宣传中似乎人均“年薪百万”的保险业,流动性也很高。“入行10个人,可能过一年之后,就留下1个。”木子有一位同学刚加入,连续两个月没有签到单,0收入,连正常吃饭的钱都没有。
也有因为各种现实因素,打算离开香港的人。
27岁的舒舒,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在加拿大做过交换生,又赴香港读硕士,最后留在香港,做与金融相关的审计。入职以来,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最难受的时候,她的身体熬垮了,住了一周的医院,心里却还在咀嚼着老板对她业务能力的批评。

香港住宅区。(图/pexels)
事实上,香港职场本身就是东亚模式的底子,OT(Over Time,加班)文化盛行。虽不强制加班,但工作强度大时,也只能“自愿”加班。
加上她在香港的房租接近一万,但基本工资也只有一万多,基本存不到钱。漫长的读书投入后,现在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曾经期待的,舒舒打算放弃港漂生活了。
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在香港读过硕士的仁桑,在符合香港人才引进条件的当口,摇了摇头。他曾住在新界的大埔,“就是《赌神》里周润发摔成傻子的地方”。但生活并非艺术电影——仁桑爱好打排球,在旺角的花墟球场,他用英语加入了打球的队伍,当球友向他询问联系方式,发现他是内地人时,叹了口气,“哎,一个北佬!”
语言、身份之外,内地人到港后,还会有生活上的不适应。仁桑租的是一间“百尺吉屋”,两米宽、五米长的屋子里,“卫生间比高铁厕所还小,墙上挂着个小热水器,我得猫着腰凑合洗澡”。房间没有宽带,读书的日子,他都是去学校和麦当劳蹭网。
仁桑感叹,香港曾经是华语文娱中心、世界电影中心、传媒中心,但现在作为一个文科生,他没办法找到一份薪资和劳动相匹配的工作,“即使很努力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无限游戏
高才计划推出一年半,随着第一批高才赴港工作和生活,新的融合正在发生。
让吴达松口气的是,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态度整体发生了变化。“我原先在香港说普通话的时候,那些服务员对我爱搭不理,但现在整个香港的服务行业至少认识到了内地人的购买力,更别提还有很多香港人开始去深圳租房和消费。”
菲菲的香港同事也经常会去深圳购物和吃饭,使用美团和大众点评也很熟练。因为知道她玩小红书,同事们也在好奇地打听她的的社交媒体账号。
她尝试与同事有更多对话,虽然英语水平不错,也突击了“粤语”,但在和同事吃饭聊天时,还是会接不上话,有种扮演“低配”版自己的感觉。

(图/《年少日记》)
有一次,聊到新电影《年少日记》时,一个香港同事说,家长希望小孩能够做得更好,不是什么错事儿,菲菲有不同意见,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用粤语讲明白,她急得问,“你们能接受我用普通话和英语吗”,最后用三种语言的大乱炖,稀里糊涂说完了。
对于张晨来说,并不存在特别的需要融入的问题。“以前同事之间都是亲疏有别,现在感受到的是,无论你是谁,都会礼貌相待。”她很喜欢香港同事之间,哪怕工作没有任何交集,大家也会有很友善的态度。
刚去香港的时候,张晨买了只金渐层,想要复制以往在北京独居养猫的那种模式,获得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坦白说我面临着很大的变化,所谓个人‘周边’的重新建立。”但她很快发现,猫不一样,人的心境与需求也不一样了。很多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她很少有时间在家里陪伴那只活泼的小猫,就为它找到了领养人,一位同样需要陪伴的在读博士生。
对于张晨来说,生活是一个游乐园,她拿着单程票进场,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去体验更多的项目。“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以前梦寐以求的事情,后面发现都不过如此。”现在的她不再追求过于抽象的目标,希望更加活在当下,“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在一个不那么忙碌的环境里,她想慢慢去了解香港,学好粤语,还想学习冲浪。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图/pexels)
吴达也把生活比喻成一场游戏,他喜欢的是无限游戏。以前在投行和大厂工作,经常会有新的项目来,在有限的游戏里,副本是在不断更新的。但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上班的副本已经变得很固定:“每天去公司把一个游戏打开,从0级打到80级,循环往复。”所以,去香港工作,是希望重新打开无限游戏。
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同样在保险行业的Michael,工作接近半年,已经在招人做团队。他拿的是带底薪的工资,因此必须完成相应的业绩。如果连续不达标,会被辞退。Michael开始更加频繁地去各个地方学习,接触更多客户,继续挖掘内地市场的潜力。
尽管已经离开,仁桑还是很怀念香港。他喜欢那里人性化的公共设施和悠闲惬意的风光,想念和朋友们散步、爬山和打沙滩排球的时光。在香港的康文署网站上,可以查询到各种类型的运动场地。他时常回想在花墟球场打完球的画面:眼前是一片自由活动的大草坪,旁边的公共澡堂,流浪汉和运动员,都在那里排队洗澡。
菲菲在香港的工作已经很稳定,在公司帮忙缴纳强积金的情况下,她还是在内地给自己买了社保、公积金,“这钱我现在交得也挺困惑,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交,也不知道能不能断,但是我就这么继续交着”。这似乎是给她自己一种安全感。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