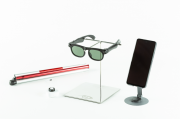原标题:“海归青椒”卷入学术江湖中 充满了不确定但又充满了机会
祝杰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到晚上10点,对他来说,加班是常事。即便是周末,祝杰还是按照一贯的工作节奏,再来实验室待上4个小时处理数据,度过忙碌又充实的一天。
他所在的科研院所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九晚六”,但除了早会之外,祝杰已经习惯了在早上10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如果实验进行到关键时刻,工作到十一二点也很正常。”他说。
在国内本科毕业后,祝杰继续到美国求学,此后8年,祝杰先后拿到了理工科硕博学位,并在美国的科研机构做博士后。
因为疫情,原本打算做三年博士后的他提前一年回国,到一家科研院受聘为助理研究员。受益于科研院所所在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祝杰获得了丰厚的补贴、落户便利和子女教育优待等优惠政策。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的科研发展水平逐渐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选择回国任教。祝杰所在的科研院所有80%的青年科研人员是海归博士,他们都曾发表相当出众的论文代表作,“即便是在国内读博士的同事,基本也都在博士毕业后去国外做了2到3年的博士后,竞争非常激烈。”他说。
像祝杰这样在海外读完博士或做两三年博士后回国的青年学者,学术圈通常称之为“小海归”。不同于那些回国时风光和抢手的“大海龟”们,他们在国外耕耘多年,组建了成熟团队并做出了卓越学术成果。“小海归”们回国后才正式开启独立的学术生涯,他们在国内的起步过程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01
第三次“海归潮”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马臻教授在2009年11月回国任教,此前他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并投递大学教职,他亲历了金融危机下的职位缩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市场非常冷,很难再申请到合适的美国大学教职。”马臻说。不久后,他申请到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2012年,朱佳妮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硕士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任教。2013年,她先后获得了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上海浦江人才计划、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科研起步基金”等多项资助。
“对于‘小海归’而言,不仅能通过这部分启动经费购买研究所需的一些专业书籍和电脑软件,而且还能够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这类普惠型的经费保证了他们即使没有第一时间申请到各级各类竞争性的课题经费,同样能够启动自己的研究。”朱佳妮说。
朱佳妮回国时,她所在的学院每年还只有一两名海归青年教师入职。而最近几年,博士人数不断增长,岗位竞聘的门槛也水涨船高。现在,朱佳妮的许多新同事不仅仅在国外取得了博士学位,还在国外做了博士后,还有一些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
“从2008年起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海外学术人才回国热是中国的第三次‘海归潮’。”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涛在《“海归”之道:中国青年学术海归的特征、动因和效应》一书中指出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前两次“海归潮”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海外留学生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以及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再次吸引大批留学生回国。
而2008年对中国科研人才从“流失”转变到“回流”、“循环”是至关重要的一年。美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青睐的留学国家,但在这一年,金融危机自美国爆发、席卷全球,美国社会陷入经济衰退,失业人数急剧增长。孙玉涛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促成了中国的第三次“海归潮”。
一方面,当时国外留给青年学者的科研机会惨淡,另一方面,国内学术圈正孕育着机遇。孙玉涛认为讨论第三次“海归潮”必须提及的两位学者是施一公和饶毅。2007年9月,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回到北京大学。2008年2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施一公回到清华大学。“两位讲席教授在美国的事业非常成功,并不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职业或者工作危机而选择回国。”孙玉涛在书中写道,施一公也曾公开表示,“要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改善国内的学术环境。”
施一公、饶毅等一批杰出学者的回国,促进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的制定和实施。2008年12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正式实施,计划提出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营造尊重、关心、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环境和氛围,吸引他们回国创新创业。
与此同时,在众多学者对遴选过程应更关注学术潜力的建议下,2010年12月,“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正式启动,开始吸引海外青年学者全职回国从事科研工作。自此,从国家、省市到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陆续为吸引海外学术人才制定了多种多样的激励计划,配备以丰厚的启动资金、奖励机制和生活补贴。在这种“外推内拉”的环境之下,这十年来,回国继续学术生涯逐渐成为了海外博士生的优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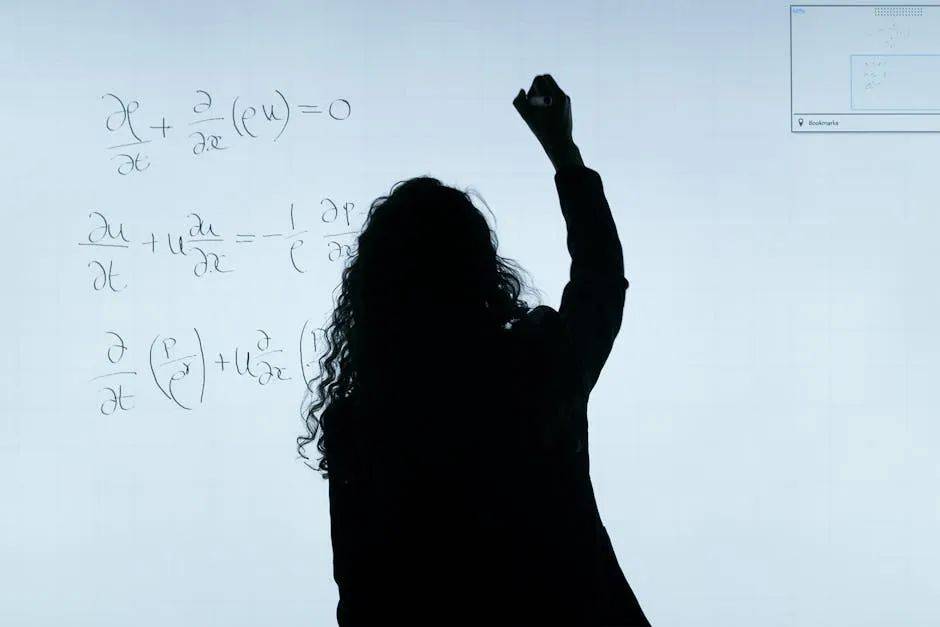
02
考核重压之下,“非升即走”
打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级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招聘网页,你会看到在对35或40岁以下青年学者的招聘要求中,往往会在职称前增加“预/准聘”的定语。
“预聘-长聘”制是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近年来一项重要的人事改革,它借鉴的是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在美国的顶尖高校,“Tenure-Track”为新录用的教师规定了考核期,教师需要在考核期内做出足以证明自己学术能力的成果,通过考核后便可以转为终身教职。
据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985高校与新进的青年教师签订的都是“预聘-长聘”合同,邱雨便是其中之一。2020年,邱雨从英国博士毕业后在国内某985高校担任讲师,她介绍说,在与学校签订的合同中,对她要求在考核期内发表论文的数量、申请的基金级别都有明确规定。
国内的“预聘-长聘”制在知乎、小木虫等青年学者活跃的平台上被称为“非升即走”,即通过考核就可以得到晋升,没有通过就只能残酷走人。
自2014年清华、北大改革试水,到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推行这一制度,学术圈对“非升即走”的优点和弊病始终争论不休。今年两会上,更有代表对“非升即走”提出意见,认为也许会催生急功近利的学术态度,不利于青年学术人才系好科研生涯中的第一粒“扣子”。
对国内“非升即走”的诟病,主要来源于和美国高校学术制度的对比。美国高校Tenure-Track的竞聘难度很大,高校会对Tenure-Track的候选人进行充分评估,当认为候选人即便在教课、做研究,还有可能刚组建了家庭需要照顾孩子的这些压力下也能做出成果,才会去录用。并且Tenure-Track的晋升名额是可以确保的,当候选人几年后通过了评审,就一定能够转为终身教职。
而国内实行的“非升即走”更接近于一种淘汰制,即便达到预定的要求,也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晋升,这是该制度本土化后最残酷的地方。

“国内高校的院系每年的晋升名额有限,有时候很可能是三四个人要竞争一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做出了出色的学术成果,能不能留下很可能也要看一同竞争人的实力。”马臻说,他也在媒体发表过文章,呼吁将这一制度的考评模式优化为“非留即走”,即把留校和晋升机会剥离,更好地维护教师利益。
海归青年教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就意味着要在规定的评价体系中取得更好的成果,这使得他们在回国后需要面对另一重考验——适应国内的学术评价标准。
2017年,朱佳妮开始研究高校“海归青椒”的职业发展课题,她访谈了五位在国内高校任职的文科青椒,当时访谈对象普遍对职称晋升和学术评价制度不太认可,尤其强调“唯论文数量论”难以全面评估尤其是人文社科教师的科研绩效。
朱佳妮在德国读书时,导师告诉她最好的学术作品应该是博士学位论文,她另一位理工科的朋友也告诉她,导师不希望学生盲目为了数量发质量不高的论文。“德国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今后成为了不起的学者,别人会把你所有的论文都找出来读。如果有一篇很差的,你的学术能力会受到别人质疑,学术声誉也会受损。”朱佳妮说,但这种观念会在国内的评价体系中受到挑战,“首先就是回国应聘高校教职的时候,如果手上已发表的论文不是那么多,竞争优势就不明显。”
2018年7月,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督促高校和科研院所改变以往“唯论文数量论”的模式,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探索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标准。朱佳妮认为,这几年国家的科研评价体制是在调整和变化的,更加看重学者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鼓励学者花费更多精力打磨好代表作。
但入职一年多的邱雨依然被考评体系的条条框框困扰着。在英国,文科博士通常会三五年内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成书,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本专著。“修改出版的过程并不容易,要求一点都不比期刊论文低。但在我们学校,这项工作不算在我的KPI里。”邱雨说,任职于另一所高校的一位“海归青椒”朋友,最近刚刚把导师的一本著作翻译成中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也不算在她的KPI里,就是纯纯地为爱发电。”

03
不一样的学术江湖
牵扯教师们学术精力的还有繁琐的行政事务,这也被很多青椒看作是国内和西方高校在管理上的最大差异。
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高校,院系行政和教师的关系相对疏离,做科研的教师几乎不会被行政事务所打扰。在美国,院系的秘书、助教等能够给Tenure-Track考核中的教师提供配套支持,分担行政和授课压力,减轻教师负担,帮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学术研究。
但是在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行政权力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师高效、专注做科研的掣肘。“我所在的单位也会说‘我们要以科研人员为中心,行政要为科研人员服务’,但是当大家分办公室的时候就发现,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永远是最好的。”祝杰说。
在邱雨的院系中,纯行政职务的人员占到三分之一,而她本人一边要接受“非升即走”的严格成果考核,一边还要因为系里教研人员不足而教授4门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不仅没有觉得行政服务到我,还会经常被他们管头管脚,提交各种报告,他们就像是你的领导一样,这对我来讲是最不舒服的地方。”邱雨抱怨道。
除了要花费精力应付行政人事,“海归青椒”还需要在新环境中摸索并建立新的学术人脉网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圈都很看重和其他学者间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交网络有利于学者间建立科研合作,尤其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而“海归青椒”在国外求学多年,导师、同门等学术人脉在他们回国后很可能支持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青年学者从研究生开始就要慎重考虑未来的学术发展路线,提前为回国发展做好规划。

祝杰因为妻子在国内工作,读博时就决定要回国工作,所以在毕业后选择到和现在任职的科研院所有战略合作的美国实验室做博士后,为自己建立和国内学术圈的联系、回国求职和适应国内的学术氛围打好基础。
在实验室,祝杰现在和美国的博士后科研院所依然有很多合作,人脉关系也从国外延续到了国内。“我现在的老板就是我前老板的老板(注:研究生通常将导师戏称为老板),很多同事都是从我博士后的实验室回来的,大家都很熟悉。”
邱雨硕博都在英国攻读,回国后又进入一所陌生高校,因为缺乏在这所学校的学术联结,即便已经回国一年半,她依然会有一种“无根浮木”的感受。
这其中也有人文社科学者不同于理工科学者的特点,人文学科的老师通常不用在庞大的课题组中做研究,这使得邱雨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疏远,“有些同事可能一个学期见不到一两次,但他们可能也是这么想我的。”唯一能让邱雨感到慰藉的是,她还能与其他从英国留学回来、进入高校的青椒朋友们抱团取暖,“但这种支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支持,并不会有资源上的转化。”

04
再适应过程被忽略
已有的研究和报道更多关注到,留学生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国家求学时,会经历对异国社会、文化环境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当博士们在国外学习过一段时间后,由于回国任教表面看上去是回到熟悉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继续做学术,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能够很快地投入高校的教研中去,海归的再适应过程在很多时候被忽略了。
朱佳妮阐释了两种适应过程的区别,出国跨文化适应过程主要是以学生的身份在异国环境下完成学业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逐渐适应了所在国的学术评价机制。但是不同国家的学术体制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海归”回国后还面临着对中国学术体制和科研评价体系的适应,需要去了解新的工作环境对教研人员的期待。
“做博士生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被包容做一些小众的、没有那么‘有用’的研究。”朱佳妮说,但身份切换到青年教师之后,很大程度上要兼顾到所在的单位环境和组织对他们的期待。作为青年教师,会卷入教学、科研还有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之中,因此不能再像国外读博时那么闲适自由。
显然,“海归青椒”在回国再适应中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跨文化层面,还来自从博士生到青年教师的身份转换。对于这些一路读到博士的青年学者而言,当他们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从学生到职场人的社会化过程。
邱雨要统筹好备课和写论文之间紧张的时间管理,刚开始工作时,她最害怕的事是上课迟到。邱雨开设了一门早上10点,有160多名学生选的大课。她每天从6:30开始定上一排闹钟,以至于手机振动一度都成了她“刻在DNA里的恐惧”。
马臻回国任教时已经在美国生活了8年,尽管是回到母校工作,但对于如何任教,他形容自己仍然“像个新生的婴儿,来发现人世间的一切”。
他谈到刚工作遇到过的种种困难,比如妻子怀孕生育,难以平衡家庭和事业,备课没有经验、研究生科研状况不理想等。马臻认为,这是一种职场新人所必然要经历的考验,对“海归青椒”的成长不一定是坏事。“这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要的是适应事业发展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总归会有一些好的结果。”他说。
祝杰是所在实验室里“比较卷”的那种人,他从读博时就已经习惯工作到深夜,在美国做博士后时,实验室里的大部分外国人会早上9点来,下午6点走,祝杰则会早上10点到,晚上八九点才离开。到现在回国一年半,他的工作生活节奏和在美国时没有明显差别。
“虽然很多青椒会喊压力大,但我能够认清自己的需求,选择来这里也是因为追求和这个工作岗位相匹配。”祝杰说,虽然对国内的学术体制有所微词,所在单位的管理体系不够科学,但祝杰也从中看到了个人发展的机遇。
他认为在国外更加成熟的科研体系中,每个职位都有明确职责和流程,祝杰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按部就班地做学术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相反在国内,虽然现在更加辛苦,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他形容目前的状态“充满了不确定,但是又充满了机会”。
*文中祝杰、邱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