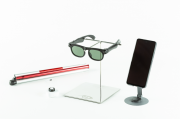原标题:从教化到人化的语文 语文课兜兜转转的这一百年
想要真正理解并尝试改变语文课之前,我们或许更应该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语文没有被独立设为一科,它向来和思想道德教育相交,儿童从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开始识字,并逐渐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

从私塾开启语文学习的儿童,每天只需被认字和背书两大任务支配。文章读不读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背下来,不然可要被先生打手心了。
长大成人后一度雄霸语文课本的鲁迅,也曾对自己的私塾经历感到后怕,他将这种陈旧的灌输式教育比作“吃人”。
到清末新式学堂兴起之际,新的教学方式和教材也应运而生。
19世纪末,国内最早的新式学堂语文教材《蒙学课本》在南洋公学诞生,它既收录了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有中国传统思想理念,文字通俗易懂,褪去了曾经的高冷滤镜。
某儿出游,见雏鸡独行,狸猝至,欲攫之,雏鸡叫,母鸡闻声驰至,以喙啄狸,狸乃去。
——选自《蒙学课本》二编第一课
在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后方,附带了一个思考题:母护其子,子当何如?
没有统一答案,让学生发散思考,是当时语文教学的一处创新。此后,许多学堂开始效仿并孕育出了各种新式教材。
1912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教育提出了“智能”上的要求:“国文要旨在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言下之意,语文更应讲求对人在智能、知识、情感以及思考上的多重启发。
从那时起,它也不再仅仅被当做一个单向推着人往前走的教化工具。
往后20年中,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新思潮的带动下,语文课本还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之变革、允许各省自行编制的过程,一批优秀教材由此诞生,百花齐放热闹非凡。
1932年,纯白话文的《开明国语课本》面世,编辑这本书时,作家叶圣陶觉得这项任务比出版自己的小说要忐忑得多。
于他而言,这是担责任的事,如果有什么荒谬的东西包含其中,恐会贻害了万千儿童。
叶圣陶希望《开明国语课本》能成为“真正适合孩子的课本”,它不单是课本,更是一种教育,但并非为了说教或应试。
柳条长,桃花开,蝴蝶都飞来。菜花黄,菜花香,蝴蝶飞过墙。飞飞飞,看不见,蝴蝶飞上天。
——选自《开明国语课本》
课文中用小故事、游戏和对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和思考,还有儿歌童诗、话剧、校园新闻、书信等实用文。
为了让课本更亲切可感,叶圣陶请朋友丰子恺帮忙,他们一人编写组稿,一人誊抄插画,共同完成了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四百余篇课文。
《开明国语课本》
有人说,即便抄写得再认真,也难比印刷来得工整。
但如果少了份这样执着的匠人精神,那时的学生或许会错过一本可亲可爱的语文书了。
语文课,兜兜转转一百年
允许多种教材并存推动了优质课本的竞争,另一方面,出版社为盈利而频繁更新版本,则伤害了语文教育本身。
同时,时代一边激发着语文的活力,一边也给越来越明显地给它留下烙印。
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和解放区各持不同教材,两者在选文上针锋相对,语文书沦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论战地。
语文课本是时代的一处载体。
又如在1958年,大跃进进入课本,语文被赋予了“年内扫除文盲”的新使命,学习进程仿佛开了10倍速,当时官媒的社论文章一经发表即被纳入课本,许多内容没有先经受时间的检验,就成了学生的教材。
小高炉,小高炉,红红的铁水往外流,大家一齐捡废铁,炼出钢造好“铁牛”。
学生们还被鼓励写大跃进民歌、万字文,学习空洞机械的作文套路。这些过分激烈的动作,对学生的语文能力造成了伤害。
识字量少,作文写不通,文言文不会读、读不懂,成了那时学生的通病。
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科书。
1978年3月,教育家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批评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后被要求重编课本,教材同时恢复全国统编。
这年秋季开学,中小学生收获了一本新书,《春晓》《咏鹅》《锄禾》等活泼、贴近生活的内容进入课堂,教材对外国文学也放宽标准,不再局限于苏联作品,《马说》《口技》《卖油翁》这些生动的文言文也跃然纸上。
1985年,国家允许统一教学大纲下多样教材并存,语文课本再次向多元和开放出发。
在教学大纲上,90年代也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新世纪以来,语文课本在一边面向和吸纳新鲜血液,一边也肩负着应有思想教育使命的同时,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受到的争议也从未减少。
人民教育出版社网上最新版小学语文教材。
自去年秋学期起,国内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开始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教材,课本自此再次回归统编时代。
既要扛起时代递来的大旗,又要及时回应频繁迭代的新兴文化,语文教育忙碌辗转了一百多年,到底向前走了多少?
语文应该是什么样子?
雪化了是什么?有孩子答是“春天”,这个回答被老师画了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水”。
《三国演义》最聪明的人是谁?有学生说是“孔明”。还是错了,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在纪录片《百年语文》中,有这么两个关于当下语文教学的案例。很显然,如果长期以这样的方式和语文相处,孩子们不免会感到打击和委屈。
困惑的事不止于此,从小学低年级到高年级,再到初中高中,语文会继续出现在查不完的近义词和反义词词典、改不完的病句和标点里,出现在“这句诗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基调”里,出现在“这篇阅读体现了什么中心思想”里,出现在要有足够正能量的800字里。
感到无奈的也不只是学生。将一篇有血有肉的文章,肢解成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技巧,并非所有语文老师的本意。
既然如此,双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也不难,是为了考试。
作家叶开曾在《对抗语文》一书中讲到,一个考试得128分的学生,其语文水平不见得比115分的学生高。而粗糙的分数却暴力地区分了这两位学生的等级。
他提出,正是那些量化、僵化的考评,以语文教材与课堂为载体,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逐渐物化了教育者,也物化了被教育者。
对于身处应试大背景下的师生来说,上述流水线几乎不可能避免,语文自身也绕不开这条路。
纪录片《百年语文》里,有一线老师努力想将学生引导向更广阔的语文,但他们深知,个人的努力毕竟渺小,这份努力或许能在个体上奏效,但很难成为一种新的通途。
也有人选择在外围做些尝试,语文老师严凌君选编《青春读书课》,希望学生通过丰富的课外阅读,获得一种自我追求的动力;他也在学校开设选修课,想为学生呈现语文世界里更多值得期待的东西。
因为“语文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和语文本身一样,没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