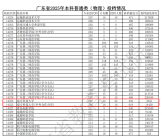原标题:杂技少年的“逃跑计划” “集体出走事件”已经过去一周多
“集体出走事件”已经过去一周多,5月中旬,15岁的华子重新回到学校。他穿着簇新的红黄相间的初中校服,参加了三门考试,英语、历史和政治,很多题都不会做。考试前,老师特意安慰他,“能做的尽量做,做不了就慢慢来”。
5月1日,“以他为首”的4名吴桥杂技少年在成都演出期间,集体出走失联。四人中,华子15岁年龄最大,弟弟强子12岁,小鑫14岁,年纪最小的小豪只有11岁。他们于4月下旬被从河北吴桥送到成都进行商演,遭遇了一位让他们害怕的成都经纪人曹涛。孩子们告诉媒体,曹涛不给他们吃早饭,练功到深夜,表演失误则惩罚四人做500个俯卧撑,甚至多次辱骂他们。

难以忍受的孩子们选择了逃跑。5月7日,四人全部被找到,由各自家长带回了贵州老家。目前,华子被贵州省毕节市竹园乡安排在当地一所中学读初一,弟弟和小豪在小学复学,小鑫被妈妈带去了贵阳。四人都不愿意再回去学杂技,除了训练辛苦,华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更害怕以后出去演出,“遇到第二个、第三个曹老板”。

杂技少年出走引发热议,学杂技出身的青年演员邢菲在微博发文,呼吁社会关注杂技少年的处境。她回忆自己从小练功经常被体罚,“高跟鞋踹在我尾椎骨的滋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杂技这个古老的行当,也被拎出来重新检视。一些传统行当的培养模式,一直游走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灰色地带。
摁下手印后,孩子就被带走了

毕节多山,华子的家在一个半山坡,坡面横切出一个平台,盖了4间平房。华子和弟弟住一间,大姐和妹妹住一间,父亲睡另一间,最外侧是厨房。院子没有外墙,前面是个半坡,走下去便是村里的干道。
华子说话低声细语,对采访有问必答,一位多次接触华子的乡干部也注意到,“这孩子比较腼腆,听话,也不反驳你”。但另一面,华子和弟弟多次离家出走,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问题少年”。
父亲王丰发现,大儿子“性格蛮好,脾气也蛮好,又不会惹祸,但读书读了几天就(出)走了。老师问他要不要上学,他说要,但过几天就又走了”。过去四五年,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带着弟弟离家出走。最长的一次,过了四个月才被派出所找到。每次出走也毫无征兆,有一次,王丰在家里洗衣服,他看着华子带着弟弟走远了,刚反应过来追出去,已经不见人影。
更多的时候,王丰不在家。妻子出走多年,他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去年两人离了婚,房间里的结婚照还没有撤下去。他平日开车载人拉货、做水泥工,如果周围乡镇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会过去吹芦笙。忙于生计已经耗费太多精力,他至今也没真正问清楚儿子为何频繁出走。
贵州省毕节市竹园乡,逃跑杂技少年华子的家。摄影/本刊记者杨智杰
华子记得,他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0岁。当时妈妈在外面打工,他听说是在毕节,离竹园乡不远,就带着弟弟去找妈妈。两人不识路,沿着公路不知道走了多远,最后被警察带了回来。四五年里,华子意识到,妈妈把他们丢在了家里不管不顾,不再想找她,但离家出走却成了习惯,“感觉出去挺好玩的”。很多时候,他和弟弟在大山里闲逛,没有钱,饿了就摘果子吃,也曾靠捡垃圾为生。
两个儿子让王丰愁苦不已,但这些孩子,却是杂技团的重点招生目标。吴桥的一位杂技团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杂技训练太辛苦,吴桥本地的孩子几乎都不再从事杂技行当,招生难是近些年整个行业面临的困境。杂技团多去周围贫穷的村镇,甚至不远千里去西南省份或是去有人脉关系的地方招生。一家吴桥当地杂技团网站的招生启事甚至明确提到,面向厌学、逃学、辍学的留守儿童,问题少年以及贫穷儿童招生,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融入社会后自食其力”。
在吴桥县职教中心一位负责教学的老师看来,杂技团的招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杂技团招收的孩子,多来自单亲或离异家庭、甚至有些是孤儿。“一些学者看到新闻就会心疼孩子,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杂技团把孩子接出来,培养杂技技能,管吃管住,家长们减轻了负担。甭管学几年,孩子到时候就能挣钱,可以缓解家庭的贫困状态。对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来说,这是他们的一条出路”。
2020年6月中下旬,河北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团团长高文军带着一位老师开车来到了贵州省竹园乡。他找了一位当地的熟人作担保人,以“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培训中心”和“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的名义招生。据了解,高文军的杂技团中,一半的孩子来自贵州,剩下一半来自河南和云南。贵州是一个“理想”的生源地。一位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每家至少有两个孩子,年轻的父母多出去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在村子里。只有一部分孩子能通过上学改变命运,更多的孩子重复着父母一辈的命运,在山里打工或是外出务工。
担保人带着高文军找到了王丰,建议“孩子不听话,可以让他们去这个学校学习”,他说自己曾去河北参观过学校,条件很好。王丰记得,高老师介绍“孩子能学习武术和杂技,包吃包住,毕业后包分配”。但是他起初没同意,“我又不认识高文军”。没过几天,三人再次上门游说,11岁的强子听到介绍,哭闹着说想报名。王丰拦不住,因为相信担保人,和高文军签了《免费学员合同》,摁下手印后,强子就被带走了。
高文军还去了竹园乡的另一个村子。郑琴家有三个孩子,担保人上门,告诉她和丈夫,“这是国家办的学校,孩子们过去可以学舞蹈和杂技,学文化课,包吃包住。要是愿意可以去,不愿意也就算了。”郑琴没读过书,不知道杂技,甚至以为这就是跳舞。对她来说,送孩子学舞蹈是件奢侈的事情。她所在的村子盘踞在一座山上,孩子学舞蹈,要送到最近的大方县县城,开车近1个小时。而且她和丈夫周末也要打零工,没有时间更没有钱。
涉事的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团外景。摄影/本刊记者杨智杰
最后,老大不愿意离开家去遥远的北方城市,10岁的二儿子小豪却被打动了。担保人给他们读合同上的条款,郑琴不同意,孩子太小,她想留在身边,但丈夫执意在合同上签了字。前后不到两个小时,郑琴就看着丈夫也上了高文军的车,送儿子一起去了河北。
留在家里的华子又出走了两次。他曾提出想辍学去学修车,王丰给他找了师父,不到两个月,又跑了。去年9月,华子回到家,听说弟弟在河北过得还不错,主动提出想去学杂技。“我对他说,给你一星期时间考虑清楚后,你想干什么我都支持。”王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周后,王丰收到儿子肯定的答复,他给高文军打了电话。没过多久,高文军再次来到竹园乡,把华子带去了吴桥县学杂技。
练了7个月“蹬人”
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两省(河北、山东)三市(沧州、衡水、德州)的交界处,开车近三天才能到竹园乡。当地自古土地贫瘠,人们多练习杂技,在农闲时外出卖艺,被称为“杂技之乡”,“吴桥杂技”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如今,杂技仍是当地人谋生的一个重要方式。吴桥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桥县有30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杂技文化旅游的人数超过3万人,有97家杂技团。
在当地,办个杂技团和开个小饭馆差别不大,是个营生。大多数杂技团是个体经营,在自家开辟场地训练和培养学徒。在当地4A景区“杂技大世界”附近,可以看到八九家杂技团的门店,一些店里,有几个孩子就在客厅练基本功。
更多的杂技团分散在县城周围的村镇,涉事的高文军的综艺杂技马戏团,就位于距离杂技大世界十几公里外的铁城镇。5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综艺杂技马戏团,从外面看,只是农村的一户普通人家,只是临街的外墙上仍有褪色的“吴桥杂技艺校”暗红色贴纸,透过窗户能看到一个大练功房。此时,屋里空无一人。
去年9月底,华子最早被带到了这里,他们称之为“老家”。节假日,杂技团三四十名学员在老家训练。平时他们都在县城里的吴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以下简称职教中心)练杂技,周日的上午和下午上两节语文课。
每天5点半,孩子们起床练基本功。最开始,华子看其他人靠着墙倒立,觉得难度也不过如此。但没过多久,他接触到第一个节目“蹬人”,才知道学杂技的不易。华子年龄大,个头高,只能当“底座”,躺在地上抬起腿,支撑一个人踩在上面。老师让一个小孩站上去找平衡,先坚持10分钟,时间慢慢增加。华子每次起身,身上衣服就全部湿透了。更让他担心的是配合不好,上面的孩子摔下来砸到华子身上,或着摔在地上伤了他自己。
华子在杂技团学了7个月,除了春节休息2天,他和其他孩子每天都在训练,晚上8点左右睡觉。春节休息的两天,孩子们就坐在老家的院子里、屋子里闲聊,不能出门。高文军招生时,曾许诺会带他们去逛公园、看风景,但大家到了以后,发现哪也去不了。
华子练了7个月的“蹬人”,和弟弟强子、小鑫、小豪也在练习合作的节目。四人练得快,临近“五一”黄金周,高文军决定让他们去成都演出,他们称之为“实习”。此时距离他们接触杂技不到1年。一位吴桥退休的杂技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出表演和学习时间长短关系不大,“有的人学了一年多也轮不到去实习,有的人接触几个月就能出去。只要练会一些东西,就要出去表演、巩固,不能闭门造车,来回几次才能最终成为演员”。
“要不我们跑吧?”
4月20日,高文军带着四个孩子自驾前往成都,两天后到达。他把孩子交给了成都风之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曹涛管理,与曹涛夫妇共同居住在成华区的家中。4月23日,高文军离开了成都。
据吴桥官方调查,4月23日至5月1日,4名少年由曹涛安排共参加演出10场,每场约20分钟。华子记得,他们曾去酒店、KTV、庆典或者红白喜事表演,最多的一天,他们连续转场三个地方。
促使四人离家出走的原因,是曹涛的管理方式。如果没有早场表演,他们8点左右起床,晚上回到家哪怕11点,四人还要练功到凌晨1点,复习节目,做身体素质训练。华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一周多的时间,曹老板从未给他们吃早饭,转场最多的那天,四人从早到晚一天都没吃东西。“所以在第三场,小鑫失误了,上面的小孩摔了下来,表演结束后曹老板在后台骂了他一顿。”有人解释是因为太饿了才失误,但是曹老板的骂声并没有停止。华子记得,那天晚上,他们吃的是别人剩下的盒饭。
5月1日早上,小鑫起床晚,集合迟到,在路上又被曹老板骂了一路。下午回到家,小鑫偷偷对华子说,“要不我们跑吧?”其他两人也围了过来,没人反对。但整个下午华子都在犹豫,他也不喜欢曹老板,但是他们四个人一共只有200元现金,根本不够。
5月1日晚上8点多,曹涛出去喝酒,留下四人和儿子、女儿在家,嘱咐他们继续练功。“后来曹老板好像忘带什么东西,上来看到我们没有练,又大骂了一顿”。这让华子下定决心逃离,而且小鑫再次提议逃跑,三人都同意。没过多久,他们打开门跑了出去。
起初,四人沿着一条大马路往前走。有人担心目标太大,提议分两队。在小鑫的要求下,年龄较大的华子和小鑫一起,弟弟强子和小豪一起,各自拿100元,“小鑫认为我和弟弟有出走的经验,可以分别带队”。在一个路口,两队分道扬镳。华子说,没过多久,他就后悔和弟弟分开了。但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其他两个小伙伴像是落入水的雨滴,早已难寻踪迹。
协助找孩子的大川救援队成员曾对《新京报》介绍,他们通过监控,看到强子和小豪当晚一夜没睡,朝着西南方狂奔10多公里,走到了成都南站附近的商场。白天他们在商场跑着玩,累了就趴着睡会,下午从商场出来,买了个雪糕,一人一口,继续往南边走。华子和小鑫则坐公交车到了双流机场附近,当晚找了个公园休息。小鑫曾想过走回贵州,但不认识路,他们在路上闲逛,晚上找公园睡觉,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水和面包。第五天,身上的钱全部花完,华子两人开始翻路边的垃圾找吃的。
5月3日早上7点,郑琴接到警方电话,才知道儿子在成都走丢了。她更不明白,小豪明明在河北上学,怎么跑到了四川。她发动全家开车去成都,到处贴寻人启事,循着监控,在各个公园找儿子。
5月6日晚上,华子和小鑫走在一个广场,被两名便衣警察找到。5月7日下午,小豪和强子在一个公园附近被找到。郑琴回忆,见到儿子时,他像刚从垃圾堆里走出来,满身都是被蚊子叮的红包。
传统行当的当代困境
直到事发后,贵州的几位家长才知道,跟他们签合同的杂技培训中心,并非是学校,而是个人经营的杂技团。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杂技团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招不满16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但是要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大部分的杂技团是个人经营,招收学徒,凭借世代传下来的经验在家训练,很少有人重视文化教育。
5月19日,吴桥景区“杂技大世界”中的一家民间杂技团,学员们正在练习基本功。摄影/本刊记者杨智杰
2019年11月2日,在国家鼓励发展职业教育背景下,针对如何传承杂技文化,提升杂技演员的文化水平,吴桥县成立了杂技职业教育联盟(以下简称杂技联盟),并制定《吴桥杂技职业教育联盟章程》,规定吴桥县职教中心与民间杂技校团进行校企合作。
杂技联盟中,杂技团自行招收杂技学徒,全权负责食宿、专业课教学和实习实训等日常管理,职教中心负责学籍和文化课教学,为符合条件的杂技学徒注册学籍。对招收的学员,双方不收取任何费用。双方有三种合作模式,分别是联盟内各校团将学员送至职教中心统一训练、统一实习实训;教学训练由职教中心组织,实习实训由校团自行组织;文化课由职教中心“送教下乡”,各校团自行组织实习实训。
据了解,目前当地加入杂技联盟的杂技团仅10家,高文军的杂技团自愿申请加入,选择的是第二种合作模式。他招生时提到的学校,则是职教中心,职教中心为杂技团提供了专门的宿舍和教学空间训练,给他们上文化课。
上述职教中心老师介绍,学杂技的孩子比较特殊,基础差,如果严格按照正常小学和中学的标准上文化课,“就太为难他们了”。一些孩子12岁正常学龄应该上初中,但给他们讲解初中的课程,他们根本听不懂。因此,针对杂技联盟的学生,学校以三年级为分界线,基础差的孩子上三年级以下的课程,学拼音、教阿拉伯数字和加减法。基础好的学生上三年级以上的课程,教阅读、写作,加减乘除和分数等。每天晚上有一节公共基础课,包括生活技能、杂技、体育、舞蹈等内容,周六日上文化课。但是华子的描述和这名老师有所出入,他告诉媒体,只有每周日上午和下午有两节课在学语文,其余时间都在练杂技。
出走的四位少年中,除了华子入学晚未办学籍外,其余三人都是2020年注册的第一届学生,他们第一次外出,就出了大问题。“对团长个人来说,此次事件中,他对孩子的安全监管不到位,外出表演,团长作为监护人,没有全程陪同。”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5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铁城镇见到了高文军,他年近60岁,看到记者,露出懊恼的神色。目前,该杂技团的40多个孩子中,注册学籍的学生已被职教中心带走,还有几个没上学籍,暂时留在家里等待通知。他说,自己“闯了祸”,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招生时,高文军以“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培训中心”“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的名义,与家长签订《免费学员合同》。但调查组发现,高文军使用的上述机构印章,未在吴桥县公安局备案,该名称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试运行)和河北经济户籍管理系统均无法查到登记注册信息。
目前,县公安部门对高文军涉嫌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以及私刻、买卖印章等问题进行调查,给予训诫,责令悔过,收缴私刻的印章。文广旅局暂扣综艺杂技团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责令停改整顿。该杂技团也被清除出杂技联盟,由联盟妥善安置在校学生。
杂技联盟校企合作模式也被诟病。官方通报指出,职教中心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对合作杂技团的学员招收、管理工作监管缺失,学生德育教育方面存在疏漏。负责职教中心全面工作的常务副校长张宏路被停职检查。
此次事件后,除了制定报备制度,吴桥文广旅局在原有常态化检查的基础上,增加了杂技团的检查频次,一是规范培训,二是排练过程中,提高安全监管,老师要随时跟着孩子,增加监管人的安全教育,训练器材也要及时更换。
此外,高文军曾提到,送孩子去成都是实习实训,但华子都注意到,在他们表演后,曹涛都会收取上千元的表演费用。上述文广旅局的负责人提到,按规定,学校的学生可以出去实习实训,但是不允许进行商演。成都那边是否属于商演,需要当地文旅部门界定,吴桥县调查组也正在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对于杂技这一类传统行当来说,极度苦练甚至体罚的魔鬼训练模式是否无从改变?训练要从娃娃抓起,但如何避免娃娃们在无保护之下成为商演的赚钱工具?这些问题在行业内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郑琴不愿意再把孩子送去学杂技,《免费学员合同》中提到的10万元违约金,成了她的负担。一位吴桥当地的杂技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合同上写上违约金,在当地很普遍,一些团长担心孩子学几年跑路,或者被其他杂技团挖走才会写上这条,主要起威慑的作用,很少有人真正会要这个钱。另外,高文军涉嫌私刻公章,双方签署的合同也没有效力。
与郑琴的态度截然不同,华子父亲王丰并不怪高文军。去年下半年,他曾去吴桥看过两个孩子,理解学杂技很辛苦,他认为高文军的训练方式没有问题。他并非看重免费,如果孩子喜欢,有人能管教孩子并教他一个技能,即使付钱他也愿意。目前,两个儿子已经在当地学校复学,王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孩子愿意,他还是会同意把他们再送去学杂技,但前提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王丰、郑琴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