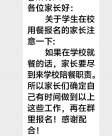原标题:缺位的性教育后 我们需要怎样的性教育?
“当我们缺少好的性教育时,艾滋病是这种缺失的体现。”方刚认为,导致艾滋病传播的无保护性行为背后,实际是亲密关系中权利博弈的结果,而对亲密关系的讨论属于性教育的范畴。

陕西省艾滋病防治方案也提出,要将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教育统筹结合。各校应利用学校医务室、心理辅导室开展性生理、性心理咨询服务。初中学段的性健康和预防艾滋病教育应融入到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生物学等国家课程以及地方课程和班团队活动中。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性道德、性责任、拒绝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毒品等教育。
对于上述规划如何展开,陕西省教育厅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方案提及的防艾教育具体内容由陕西省卫健委统筹,教育厅相关部门配合,是否有具体方案、方案能否公开由卫健委统筹协调。《中国慈善家》多次致电陕西省卫健委科技教育与宣传处,但对方均以相关人员不在为由婉拒采访。
在高校层面,性教育缺口依然很大。陕西省在方案中规定,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学生志愿者等作用,开展预防艾滋病、禁毒、性与生殖健康等综合知识教育。学校要将学生参与艾滋病防治志愿活动纳入学生志愿者服务管理和学生实践活动内容,在资金、场所等方面提供必要支持。
浙江舟山,60多名孩子在定海区东管庙社区的会议室里观看教育片《青春期性心理保健》。
广东某高校学生小林(化名)发现,即使进入大学,生理健康课仅仅是全校的通选课,一学期只开放几百个选课名额,无法覆盖全校,选课人数寥寥。她问身边同学不选课的原因,大家觉得“生理卫生课没什么用”“老师讲得不好玩”。
小林曾经加入学校红丝带社团,参与社团举办的同伴教育活动。作为社团成员,小林可以定期去校外接受专业的防艾知识和性教育培训,但她认为通过这类培训获得的知识并不系统。她与社团成员在学校定期组织同伴教育活动,举办活动需要学校审批,虽然有生理健康课的授课老师帮助,但性教育类的活动通过审批并不容易。
在成功举办的几期活动中,每次来参加的学生从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不等。社团在组织同伴教育时会通过破冰游戏、即兴表演等活动打破现场的尴尬,把防艾知识融合进游戏和表演中。“大家玩得很开心,但不知道活动结束后大家是否会采取我们提倡的防护措施。”小林说。
在现实层面,教师对性教育讳莫如深,中小学性教育课处于无教师认领的尴尬境地。广东一所高校的学生小林(化名)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她的中小学时期,唯一一次的性教育课是初中时学校组织的公开讲座,讲座要求学生与家长一起参加。小林回忆,主讲人在讲座中提到“无保护性行为”“手淫”等问题。“实际上当时我们根本不太懂无保护性行为、手淫这些名词,家长在我们旁边很尴尬,拒绝给我们解释。”
山东济南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戴敏(化名)告诉《中国慈善家》,她发现学生在学习生殖与健康章节时状态反常,“有的学生起哄嬉笑,有的学生直接害羞到不愿意抬头”。 在参加完一场防艾宣传活动后,班级中有学生直呼“同性恋太可怕了”。
但推行防艾教育和性教育阻力不小。戴敏曾向校领导建议开设性教育课程,但校领导以“师资不足”“没有多余的课时”“上级主管部门暂时没有统一要求”等理由拒绝。“性教育的尺度也是学校犹豫的原因,讲得深,怕家长找上门;讲得浅,学生听不懂,这就违背了初衷。”
总结这几年的性教育实践,方刚说,即使有2000个家长支持,只要有一个家长反对,学校也会选择不去做。
与此同时,不少专家呼吁,将青少年性教育前移。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曾表示,当前青少年发育越来越早,能够接受性信息的渠道也五花八门,尽早将性教育纳入中国学校的教学体系也越来越有必要。如果等到大学才开设系统的性教育课程,只能算是“补课”。在2020年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凌峰也呼吁,将儿童性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在方刚看来,性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涵盖性别、亲密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性教育应该是让孩子做出负责任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格成长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不应该采用规训的方式,不要一味告诉孩子不能做什么。“我们的性教育不是用来防病的,也不是用来阻止恋爱的。需要开放、开明,所有事情都可以拿来讨论。”